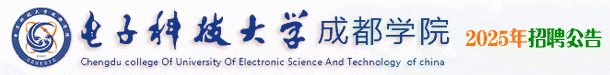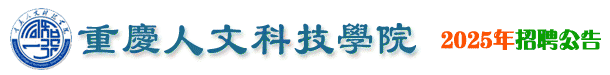就业是国计民生之根本,没有就业,经济增长成效何以体现,社会稳定何以维系。
就业也是经济学研究之核心诉求,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皇皇巨著——凯恩斯之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,就是以“就业”打头。
4月5日,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除部署落实2017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外,再次将“就业”作为会议的核心议题。会议强调,“确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,坚决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硬仗。”
将“稳定和扩大就业”上升到“打硬仗”的高度,这并不是因为我国过去几年“稳就业”的成绩不显著,而是因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局部变化。
在2013—2016年的四年间,我国GDP增速处于渐进下行区间,陆续从7.8%、7.3%、6.9%降至2016年的6.7%,但是,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,过去四年,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却能够稳定(2013年1310万人、2014年1322万人、2015年1312万人、2016年1314万人),基本稳定在1310万—1322万人的区间,这显然是极其不容易的。同时,这一成绩的取得,也一举扭转了我国既往“经济增长与就业”近乎同频波动的关系。
但是,过去四年我国“稳就业”的良好趋势,却在今年遭遇到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,当然,这种变化是预料中的。其一,美联储明确进入强加息周期,这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相对被动收紧,而货币政策的相对收紧(或者说进一步“稳健”),很显然,会对夯实就业基本面构成压力;其二,供给侧结构性改革(“三去一降一补”)已经进入实质性攻坚阶段,而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”毫无疑问会不可避免地挤压传统产业的就业空间;其三,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高,在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登上700万人的台阶之后,今年将有可能迎来800万人左右的高峰,而这显然会进一步增添全社会的就业压力。
在今年“稳就业”压力陡增之下,会议要求“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同时,推出促就业新措施”,“新措施”主要有五条,第二条至第五条主要侧重于“针对不同群体的就业创业需求,给予针对性的就业创业支持”,而“新措施”的第一条,表面上看貌似缺乏针对性,事实上却最具全面统筹之效——制定财税、金融、产业等重大经济政策时,要综合评价对就业的影响,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联动,结构优化与就业转型协同。
制度变量才是纾解就业压力的核心命题。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我们制订财税、金融和产业政策时,均将GDP增长作为核心、甚至唯一的诉求,而在2010年之后,我们对相关重大经济政策的制订,在依然重视GDP增长的同时,也仅仅兼顾到单位能耗和环境等要素,但是,一直以来,我们近乎所有的重大经济政策制订,均相对忽视了其对就业影响的系统评估。
就财税政策而言,近两年,部分地方政府在加大传统基建投入时,也屡将“稳就业”作为借口,但是,一者地方政府在加大传统基建投入时,理应平衡好自身的财政收支状况、以及基建水平与地方经济的匹配度,二者加大传统基建投入对“稳就业”的促进,往往仅是一次性的、或阶段性的,这远不如释放政策红利增强当地经济的内生活力,更有利于当地中长期的“稳就业”。
就金融政策而言,尽管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占比逐年上升,但是,在整体依然过于依赖间接融资市场(以信贷为主)之下,我们过度强调固定资产担保的银行信贷政策,很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传统信贷政策对新经济、以及新兴就业市场的伤害——因为,相比传统产业,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先天依靠无形的智力资产、而不是有形的固定资产。
再就产业政策而言,还以互联网产业为例,我们可以讨论两个方面,一是产业政策有必要相对差别化,手游类企业和O2O类企业都属于互联网产业,但是,相比手游类企业,O2O类互联网企业显然可以带动更多的间接就业岗位,二是部分地方性政策,在传统的思维惯性之下,没有考虑到新经济业态对增加间接就业人数、以及灵活就业人数的促进作用,比如在汽车共享出行领域。
之于当下而言,我们有必要认识到,突破制度性阻碍,将制度变量置于研究纾解就业压力的首位,这显然不仅有利于长远,也更具改革意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