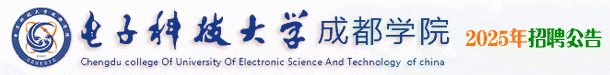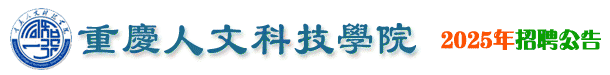一直以来,“脑残”似乎成了90后的标签。然而,在今年的互联网创业潮中,一些90后创业者却说:I don’t care,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被理解。他们信奉:“技术宅”、“向巨头挑战”、“自黑”却不怕“黑”,他们觉得“致青春”太土了,本来就没有什么单纯的东西。他们对70后、80后的集体回忆“不感冒”。
不论是“硕粉哥”张天一、“脸萌”掌门郭列,还是北大海归孙宇晨,他们在诠释90后的“理想主义”:创业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,是对理想的追求,对细节的不在乎。
孙宇晨
从北大到沃顿商学院到创业
戴着Google眼镜的孙宇晨“觉得自己这样很酷”。甚至对“装逼范儿”的“炮轰”,也毫不在意地说:“Don’t care”(我不在乎)。
1990年出生的他是锐波科技的创始人兼CEO,美国Ripple Labs大中华区首席代表。他说自己的“野心”是想构建一个新的价值网络。
回国创业新支付系统
广州日报:你回国创建锐波公司,主要做什么?
孙宇晨:Ripple labs设计了一个Ripple协议,试图让不同货币自由、免费、零延时地汇兑,创造了一个价值网络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体系。比如,现在国际电汇大概要2到3个工作日,手续费高。而用比特币可能一个小时,但在锐波网络大概3到5秒。我们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套协议在中国本土化。
广州日报:如果能推行,国际小额汇款能在网上完成么?
孙宇晨:我希望是这样,但需要银行配合。
从“三本生”到沃顿商学院
广州日报:你一路走来都是佼佼者?
孙宇晨:其实我以前学习成绩很差,在惠州读书,读到高二成绩都很差,在三本左右徘徊。高三用了一年时间,从300多分,上升到650分,翻了一倍。
高二时,我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,也是靠那个获得北大的20分加分。我觉得长期生活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,个人的自尊心被压抑了。很多人都觉得你不行,弱爆了。虽然我得了新概念一等奖,但高考作文分数还是很低(笑)。
广州日报:大学之后呢?
孙宇晨:后来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,又转系到历史系。在北大期间发生两件事:我选北大学生会主席,因为我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,比如“直选”,后来就被叫停。第二件事就是,北大推行“会商制”,把每个学生进行等级,分批进行“治疗”。我当时就批评了这个事,上了《亚洲周刊》的封面。
广州日报: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什么?
孙宇晨:2011年,我大四毕业后,去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。我的导师是沃顿商学院研究中国公司最有名的教授Marshall Meyer。柳传志都是他的学生。
从美国回来后,在中金实习,然后去美国工作,后来我就带着ripple回国了。其间,我投资了比特币、特斯拉等。
90后的标签是“无情”
广州日报:你觉得90后的标签是什么?
孙宇晨:我觉得90后是比较无情的。比如说70后、80后遇到一个产品不好,不会去找老板提意见,勉为其难用一下。就像张天一说他的父母非常不容易,早晨5点就起来做煎饼果子。但绝大多数90后会觉得:滚你丫的,做这么烂,走。根本不会给你面子,是完全残酷的市场经济淘汰法则。
广州日报:你们怎么看张天一卖米粉?
孙宇晨:几年前当时有校友去卖猪肉了,被人笑话。但现在张天一卖米粉,就没有人在意了,甚至成为一种标杆性行为。大家观念变化很大。

郭列
给大公司打工只是被分配任务
郭列是穿着一身黑色T恤,夹趾拖鞋,刘海长得差点要盖过眼睛的消瘦男孩。说起话来,略低着头,声音温柔。
他是一周内新增用户2000万,最多一天新增500万用户,App排行曾经第一的“脸萌”的掌门人。他的公司目前已确定数千万A轮融资,9名90后团队创造了估值过亿。
从“学渣”到“挑战杯”总决赛
广州日报:谈一谈你的成功?
郭列:不复杂,学习不太好。
高中叛逆期,我喜欢古惑仔,觉得很酷,当时也很脑残。不是特别听话,还打过两次架,第二次较严重,人家报警,自己也满18岁了,班主任在操场哭。我想,打架我都没哭,班主任哭什么,我很感动,也很自责。
当时有想过要不要辍学,但班主任说很看好我,家里人也没怪我。我非常感动,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班主任和家长。
后来,我给自己定目标,希望为他们考一个好大学,不是为我自己。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,晚上12点半睡觉,把手机一关,整整一年,我从一个学渣慢慢逆袭。
广州日报:顺利考上大学后呢?
郭列:很迷茫。我曾给班里同学写邮件,说不打算做本专业,上课看不到我不要太想我,现在想起来挺傻。
后来,我认识了一个做“挑战杯”创业赛的学长,他的经历,吸引我去尝试创业比赛。
我从一个人开始,到处贴传单、找人,整整一年。当时目标是希望从100多所学校中,走到全国总决赛。一年后,我们成功地闯入了全国总决赛,在上海被其他学校PK掉了。这个旅程让我觉得创业很好玩,跟团队在一起很开心。
创业瘦得让父母感觉像吸毒
广州日报:你还在腾讯工作过一段时间,为什么辞职了?
郭列:当时,我对进到腾讯的憧憬是,应该是像现在这个样子,拿着麦克风跟大家介绍我的产品。但腾讯有2万人,你只是其中之一。你有很多东西要学,更多的事是大家分配给你的,这就会有点问题。
广州日报:自己创业是不是比给人打工更有快感?
郭列:其实,做完“说说”,钱也花得差不多了,开始过苦日子了。
之前在腾讯,几百个同事,大家天天玩得很High,有很多活动、兴趣组、聚会。创业后,一个人在家里,像一个傻子,一起床走到客厅,整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,有时候变成有点儿像精神分裂,会自言自语。
另外,创业时发现钱不够用,要省着用,花6.5元吃两顿。去年创业一年,从120斤瘦到了100斤。其间,还要顶着父母的压力。本来找到工作,爸妈很开心。出来创业后,他们会很担心,有时候回去穿得破破烂烂的,也很瘦,他们感觉我像在外面吸毒。
广州日报:脸萌不可能永远是第一,现在玩的人也越来越少?
郭列: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使命,完成后不需要对它有过高的预期。
其实它是一个过程,不是结果,包括我们现在连自己玩脸萌已经越来越少了,我们觉得它已经不能让我们兴奋了,我们希望做让我们兴奋或者更好玩儿的一些事情,我们把整个创业当做一个过程,无论它成功或者失败,我们非常享受这个过程,和一群人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。

张天一
北大硕士也可卖米粉
一个北大法学硕士,卖米粉卖得风生水起。在90后CEO中,湖南常德米粉创始人张天一算是少有在传统领域闯荡的。他说:“卖米粉千万别拿互联网说事。”“90后”、“伏牛堂CEO”、“北大硕士卖米粉”这三个标签让初出茅庐的创业家张天一一时间赚足了眼球。
都搞金融谁来做实业
广州日报:6年法律专业为什么会去创业卖米粉?
张天一:读法律专业只是一个偶然,继续读研更多的考虑是拿文凭。
硕士学的是金融法,同学大多去投行工作。我在找工作过程中产生了两点困惑,大家都去搞金融了,谁来做实业?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困惑,大家都想去从事那好工作,但是有大批工作没有人愿意去做。大家都想去好地方,但结果却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到了这个好地方,更可能是堵在路上。这些困惑,加上身处异乡对家乡米粉的怀念,让我转行去餐饮行业。
广州日报:现在你是怎么理解创业的?
张天一:如果让我自己写新闻标题,我就写“创业就是一种修行”、“身价一个亿就出家”。其实对我而言,创业不是信仰,不是目的,而是一个过程。像褚时健、柳传志这些人,这么高龄了还在工作,我相信不是为了财富,我个人信佛,我更愿说创业是一种修行。
互联网提供创业机会
广州日报:你说卖米粉不要拿互联网思维说事,但互联网真的就没有影响你吗?
张天一:我们90后,本就处于互联网时代,这是我们的本能,由本能而上升到思维层次,我觉得很搞笑。
互联网代表了连接方式的改变,它改变了餐厅的辐射半径。也就是因为互联网,伏牛堂能打破传统餐饮行业地段的限制,在“一流商圈,十流位置”兴盛营业,甚至可以吸引外地湖南人开1~2个小时的车专程跑到我们店里吃米粉。
互联网对90后最大的意义在于:为我们四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,在一无所有的时候,坚持做自己的机会。在传统时代,四个小孩什么都没有,还敢叫板现实,是不可能的。在这一点我感谢互联网。
广州日报:餐饮是一个传统产业,伏牛堂未来会采用怎样的新模式经营?
张天一:未来伏牛堂有可能是一个大数据企业,在明确知道顾客群是湖南人,我们会选择去挖掘一些湖南人的数据,制造一些湖南人需要的消费场景。说不定有可能未来吃米粉是免费的,而是通过消费场景去赚钱。例如我们的制服,以后说不定我们的店一半是米粉店,一半是服装店,也许有可能,也许不可能,我不知道。